張回上一回結因,下一回成果,此回乃將因做果之時之事也。然而卻是兩段文字:一段定挨光,一段做挨光。寫十分光,卻先寫五件事,後又寫一件事,才寫十分光。而寫十分光內,卻又寫九個「此事便休了」,分明板板寫出,卻又生活不凡。且見後文,金蓮如於三分、四分光時便走,五七分時便走,王婆所云「我不能拉住他」。總之到九分光時,如若不肯,王婆亦止云「來搭救」,西門「此事便休」,「再也難成」。然則挨光雖王婆定下,而光之能成,到底是金蓮自定也。寫婦人之淫若此。
後半寫挨光,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。看他偏是照前說出者一樣說去,偏令看者不覺一毫重複,止見異樣生動,自是化工手筆。
看他於五分光成時,止用「王婆將一手往臉一摸」,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,真是異樣妙筆。
《金瓶梅》純是異樣穿插的文字,唯此數回乃最清晰者。蓋單講金蓮偷期,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,而於閒扯白話時,乃借月娘、嬌兒等攏入金蓮。一邊敲擊正文,全不費呆重之筆;一邊卻又照管家裡眾人,不致冷落,直一筆作三四筆用也。
文內寫西門慶來,必拿灑金川扇兒。前回云「手裡拿著灑金川扇兒」,第一回云「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金扇兒」,直至第八回內,又云「婦人見他手中拿著一把紅骨細灑金金釘鉸川扇兒」。吾不知其用筆之妙,何以草蛇灰線之如此也。何則?金、瓶、梅蓋作者寫西門慶精神注瀉之人也。乃第一回時,春梅已於「大丫頭」三字影出。至瓶兒,則不啻心頭口頭頻頻相照。而金蓮,雖曾自打虎過下,卻並未與西門一照於未挑簾之前,則一面寫武二自打虎做都頭文後,為單出筆寫金蓮這邊,而西門為此書正經香火,今為寫金蓮這邊,遂致一向冷落,絕不照顧。在他書則可,在《金瓶梅》豈肯留此綻漏者哉!況且單寫金蓮於挑簾時出一西門,亦如忽然來到已前不聞名姓之西門,則真與《水滸》之文何異?而敘得武大、武二相會,即忙敘金蓮,敘勾挑小叔,又即忙敘武大兄弟分手,又即忙敘簾子等事,作者心頭固有一西門慶在內,不曾忘記。而讀者眼底不幾半日冷落西門氏耶?朦朧雙眼,疑簾外現身之西門,無異《水滸》中臨時方出之西門也。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,三十分滑,三十分輕快,三十分討便宜處,寫一金扇出來,且即於敘卜志道時,寫一金扇出來。夫雖於迎打虎那日,大酒樓上放下西門、伯爵、希大三人,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線,而便不嫌半日查洋洋寫武大、寫武二、寫金蓮如許文字。後於挑簾時一出西門,止用將金扇一幌,即作者不言,而本文亦不與《水滸》更改一事,乃看官眼底自知為《金瓶》內之西門,不是《水滸》之西門。且將半日敘金蓮之筆,武大、武二之筆,皆放入客位內,依舊現出西門慶是正經香火,不是《水滸》中為武松寫出金蓮,為金蓮寫出西門。卻明明是為西門方寫金蓮,為金蓮方寫武松。一如講西門慶連日不自在,因卓二姐死,而今日簾下撞著的婦人,其姓名來歷乃如此如此。說話者恐臨時事冗難敘,乃為之預先倒算出來,使讀者心亮,不致說話者臨時費唇舌。是寫一小小金扇物事,便使千言萬語一篇上下兩半回文字,既明明寫出,皆化為烏有,而半日不置一語、不題一事之西門慶,乃復活跳了來。且不但此時活跳出來,適才不置一語、不題一事之時,無非是西門氏帳簿上開原委,罪案上寫情由,與武大、武二絕不相干。試想作者,亦安有閒工夫與不相干之人寫家常哉!此是作者異樣心情寫出來。而寫完放筆,仰天問世,不覺失聲大哭日:「我此等心力,上問千古,下問百世,亦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!」故金扇兒必是卜志道送來,而挑簾時金扇一照,成衣時金扇又一照,躍躍動人心目。作者又恐真個被人知道,乃又插入第八回內,使金蓮扯之。一者收拾金扇了當,二者將看官瞞過,俱令在卜志道家合夥算帳。今卻被我一眼覷見,九原之下,作者必大哭大笑。今夜五更,燈花影裡,我亦眼淚盈把,笑聲驚動妻孥兒子輩夢魂也。
然而作者於第二回內,不寫婦人勾挑武二哥,豈不省手?不知作者蓋言金蓮結果時,如何一呆至此,還平心穩意要嫁武二哥哉。故先於此回內,特特描寫一番,遂令後九十回文中,金蓮不自揣度,肯嫁武二,一團癡念,緊相照應。人雖鶻突,文卻不可鶻突也。然則西門慶被色迷,潘金蓮亦被色迷,可懼,可思。
詩曰:
乍對不相識,徐思似有情。
杯前交一面,花底戀雙睛。
傞亞驚新態,含胡問舊名。
影含今夜燭,心意幾交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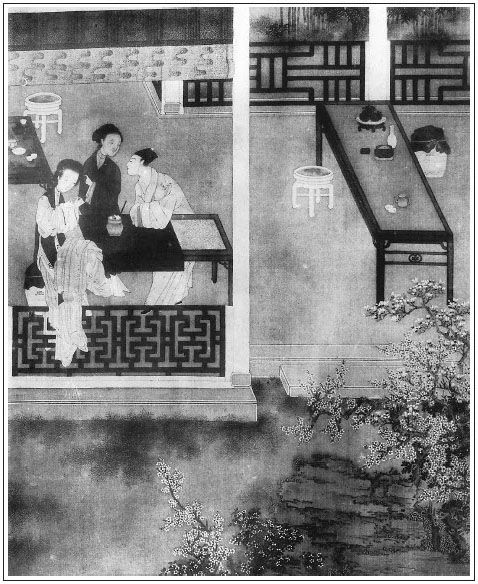
話說西門慶央王婆,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,便道:「乾娘,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,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。」王婆道:「大官人,你聽我說:但凡『挨光』的兩個字最難。怎的是『挨光』?比如如今俗呼『偷情』就是了。要五件事俱全,方才行的。第一要潘安的貌;第二要驢大行貨;第三要鄧通般有錢;第四要青春少小,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;第五要閒工夫。此五件,喚做『潘驢鄧小閒』。都全了,此事便獲得著。」張夾未有十分光,先出五件事。文字掩遇,妙絕。西門慶道:「實不瞞你說,這這五件事我都有。第一件,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,也充得過;第二件,我小時在三街兩巷游串,也曾養得好大龜;第三,我家裡也有幾貫錢財,雖不及鄧通,也頗得過日子;第四,我最忍耐,他便打我四百頓,休想我回他一拳;第五,我最有閒工夫,不然如何來得恁勤。張夾第五隻在眼前一映,便鮮活如見。做文只在拿輕放重也。乾娘,你自作成,完備了時,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:「大官人,你說五件事都全,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,也多是成不得。」西門慶道:「且說,甚麼一件事打攪?」
王婆道:「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,但凡挨光最難,十分,有使錢到九分九厘,也有難成處。我知你從來慳吝,不肯胡亂便使錢,只這件打攪。」張夾五件後又有一件,然則前雲鄧通是般有錢,此雲使錢也,有錢不使何益?故此件又第一要緊也。西門慶道:「這個容易,我只聽你言語便了。」王婆道:「若大官人肯使錢時,張夾又盡一句,總之王婆要緊事在此也。老身有一條妙計,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。」西門慶道:「端的有甚妙計?」王婆笑道:「今日晚了,且回去,過半年三個月來商量。」張夾又盪開。情生動。西門慶央及道:「乾娘,你休撒科!自作成我則個,恩有重報。」王婆笑哈哈道:「大官人卻又慌了。老身這條計,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,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,十捉八九著。今日實對你說了罷:這個雌兒來歷,雖然微末出身,卻倒百伶百俐,會一手好彈唱,針指女工,百家歌曲,雙陸象棋,無所不知。小名叫做金蓮,娘家姓潘,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,張夾略過王招宣。妙絕。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。後因大戶年老,打發出來,不要武大一文錢,白白與了他為妻。這雌兒等閒不出來,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閒坐。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,他也叫我做乾娘。武大這兩日出門早。大官人如幹此事,便買一疋藍綢、一疋白綢、一疋白絹,再用十兩好綿,都把來與老身。老身卻走過去問他借歷日,央及他揀個好日期,叫個裁縫來做。他若見我這般說,揀了日期,不肯與我來做時,此事便休了;張夾一個「便休」。他若歡天喜地說:『我替你做。』不要我叫裁縫,這光便有一分了。繡眉計料如指掌。張夾一分光。我便請得他來做,就替我縫,這光便二分了。張夾二分光。他若來做時,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。他若說不便當,定要將去家中做,此事便休了;張夾兩個「便休」。他不言語吃了時,這光便有三分了。張夾三分光。這一日你也莫來,直至第三日,晌午前後,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,以咳嗽為號,你在門前叫道:『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?我買盞茶吃。』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坐喫茶。他若見你便起身來,走了歸去,難道我扯住他不成?此事便休了。張夾上文兩個「此事便休了。」此處又添一句,生動之極。三個「便休」。他若見你入來,不動身時,這光便有四分了。張夾四分光。坐下時,我便對雌兒說道:『這個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,虧殺他。』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,你便賣弄他針指。若是他不來兜攬答應時,此事便休了;張夾四個「便休」。他若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,這光便有五分了。張夾五分光。我便道:『卻難為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,虧殺你兩施主,一個出錢,一個出力。不是老身路歧相央,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,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。』你便取銀子出來,央我買。若是他便走時,難道我扯住他?此事便休了。張夾又對鎖上一句,五個「便休」。他若是不動身時,事務易成,這光便有六分了。張夾六分光。我卻拿銀子,臨出門時對他說:繡眉井井有條。『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。』他若起身走了家去,我終不成阻擋他?此事便休了。張夾又換一句,卻一樣雙句串下。六個「便休」。若是他不起身,又好了,這光便有七分了。張夾七分光。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,便說:『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,且吃一杯兒酒,難得這官人壞錢。』他不肯和你同桌吃,去了,此事便休了。張夾七個「便休」。若是他不起身,此事又好了,這光便有八分了。張夾八分光。待他吃得酒濃時,正說得入港,我便推道沒了酒,再交你買,你便拿銀子,又央我買酒去並果子來配酒。我把門拽上,關你兩個在屋裡。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時,此事便休了;張夾八個「便休」。他若由我拽上門,不焦躁時,這光便有九分,張夾九分光。只欠一分了。張夾妙在說完九分,卻又說出一分來了。生動異常。只是這一分倒難。大官人你在房裡,便著幾句甜話兒說入去,卻不可燥暴,便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,那時我不管你。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箸下去,只推拾箸,將手去他腳上捏一捏。他若張眉內有十一「他若」,四「若是他」,錯落盡致,不細注。鬧將起來,我自來搭救。此事便休了,張夾九個「便休」。卻又放這樣幾句在上,妙絕。十分「光」,卻用九個「便休」描出,而一毫不板。奇絕。妙絕。再也難成。若是他不做聲時,此事十分光了。張夾十分光。這十分光做完備,你怎的謝我?」張夾要緊接筍。西門慶聽了大喜道:「雖然上不得凌煙閣,乾娘你這條計,端的絕品好妙計!」張夾只讚好計,與各人心事,如畫。王婆道:「卻不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。」繡旁要緊的。張夾婆子又叮嚀,只是他的心事。文入化境。西門慶道:「便得一片橘皮吃,切莫忘了洞庭湖。這條計,乾娘幾時可行?」婆道:「只今晚來有回報。我如今趁武大未歸,過去問他借歷日,細細說與他。你快使人送將綢絹綿子來,休要遲了。」西門慶道:「乾娘,這是我的事,如何敢失信。」於是作別了王婆,離了茶肆,就去街上買了綢絹三疋並十兩清水好綿。家裡叫了玳安兒用氈包包了,一直送入王婆家來。王婆歡喜收下,打發小廝回去。正是:
巫山雲雨幾時就,莫負襄王築楚台。
當下王婆收了綢絹綿子,開了後門,張夾記著,後門出現,一。走過武大家來。那婦人接著,走去樓上坐的。王婆道:「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喫茶?」那婦人道:「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,懶走動的。」王婆道:「娘子家裡有歷日,借與老身看一看,要個裁衣的日子。」婦人道:「乾娘裁甚衣服?」王婆道:「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,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,我兒子又不在家。」婦人道:「大哥怎的一向不見?」王婆道:「那廝跟了個客人在外邊,不見個音信回來,老身日逐耽心不下。」婦人道:「大哥今年多少年紀?」王婆道:「那廝十七歲了。」婦人道:「怎的不與他尋個親事,繡旁工夫全做在此等處!與乾娘也替得手?」王婆道:「因是這等說,家中沒人。待老身東楞西補的來,早晚要替他尋下個兒。等那廝來,卻再理會。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,身子打碎般,睡不倒的,只害疼,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。難得一個財主官人,常在貧家喫茶,但凡他宅裡看病,買使女,說親,見老身這般本分,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。又佈施了老身一套送終衣料,繡眉說起便及送終,此亦王婆之諱。綢絹表裡俱全,又有若幹好綿,放在家裡一年有餘,不能夠做得。今年覺得好生不濟,不想又撞著閏月,趁著兩日倒閒,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掯,只推生活忙,不肯來做。老身說不得這苦也!」張夾寫婆子真是舌上生花。那婦人聽了笑道:「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。繡旁煞是技癢。若是不嫌時,奴這幾日倒閒,出手與乾娘做如何?」那婆子聽了,堆下笑來說道:「若得娘子貴手做時,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。久聞娘子好針指,只是不敢來相央。」那婦人道:「這個何妨!既是許了乾娘,務要與乾娘做了,將歷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,奴便動手。」王婆道:「娘子休推老身不知,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,你不知識了多少,如何交人看歷日?」婦人微笑道:「奴家自幼失學。」婆子道:「好說,好說。」便取歷日遞與婦人。婦人接在手內,看了一回,道:「明日是破日,後日也不好,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。」王婆一把手取過歷頭來掛在牆上,便道:「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,就是一點福星。繡旁老奸甚巧。何用選日!老身也曾央人看來,說明日是個破日,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破日,我不忌他。」那婦人道:「歸壽衣服,正用破日便好。」王婆道:「既是娘子肯作成,老身膽大,只是明日起動娘子,到寒家則個。」婦人道:「何不將過來做?」王婆道:「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,又怕門首沒人。」婦人道:「既是這等說,奴明日飯後過來。」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,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,張夾點水不漏。約定後日准來。當夜無話。
次日清晨,王婆收拾房內乾淨,預備下針線,安排了茶水,在家等候。且說武大吃了早飯,挑著擔兒自出去了。張夾又點武大,百忙裡都照管到。那婦人把簾兒掛了,張夾簾子還有餘波,文心何其周匝也。簾子十二。吩咐迎兒看家,從後門張夾後門二。走過王婆家來。那婆子歡喜無限,接入房裡坐下,便濃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。抹得桌子乾淨,便取出那綢絹三疋來。婦人量了長短,裁得完備,縫將起來。婆子看了,口裡不住喝采道:「好手段,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,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指!」那婦人縫到日中,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,又下了一箸面與那婦人吃。
再縫一歇,將次晚來,便收拾了生活,自歸家去。恰好武大挑擔兒進門,婦人拽門下了簾子。張夾簾子十三。武大入屋裡,看見老婆面色微紅,問道:「你那裡來?」婦人應道:「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,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。」武大道:「你也不要吃他的才是,我們也有央及他處。他便央你做得衣裳,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,不值得甚麼,便攪撓他。你明日再去做時,帶些錢在身邊,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。常言道:遠親不如近鄰,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,你便拿了生活來家,做還與他便了。」正是:
阿母牢籠設計深,大郎愚鹵不知音。
帶錢買酒酬奸詐,卻把婆娘自送人。繡旁語俗而真。
婦人聽了武大言語,當晚無話。
次日飯後,武大挑擔兒出去了,王婆便踅過來相請。婦人去到他家屋裡,取出生活來,一面縫來。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。看看縫到日中,張夾又一日日中。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,向王婆說道:「乾娘,奴和你買盞酒吃。」王婆道:「啊呀,那裡有這個道理。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,如何交娘子倒出錢,婆子的酒食,不到吃傷了哩!」繡眉三字非謙,卻是定論。那婦人道:「卻是拙夫吩咐奴來,若是乾娘見外時,只是將了家去,做還乾娘便了。」那婆子聽了道:「大郎直恁地曉事!既然娘子這般說時,老身且收下。」這婆子生怕打攪了事,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,慇勤相待。看官聽說:但凡世上婦人,由你十分精細,被小意兒縱十個九個著了道兒。張夾又入幾句閒言,文字方不死板。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心,和那婦人吃了。再縫了一歇,看看晚來,千恩萬謝歸去了。
話休絮煩。第三日早飯後,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,便走過後門首張夾後門三。叫道:「娘子,老身大膽。」張夾如聞其聲。那婦人從樓上應道:「奴卻待來也。」兩個廝見了,來到王婆房裡坐下,取過生活來縫。那婆子點茶來吃,自不必說。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。張夾又一日晌午。
卻說西門慶巴不到此日,繡旁也好一等了。打選衣帽齊齊整整,身邊帶著三五兩銀子,手裡拿著灑金川扇兒,張夾金扇三現。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。到王婆門首,便咳嗽道:「王乾娘,連日如何不見?」那婆子瞧科,便應道:「兀的誰叫老娘?」西門慶道:「是我。」那婆子趕出來看了,笑道:「我只道是誰,原來是大官人!你來得正好,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。」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,拖進房裡來,對那婦人道:「這個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。」西門慶睜眼看著那婦人:雲鬟疊翠,粉面生春,張夾是數日眠思夢想,忽然相見的身份心事。上穿白布衫兒,桃紅裙子,藍比甲,正在房裡做衣服。見西門慶過來,便把頭低了。繡旁媚致。張旁一低頭了。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。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,還了萬福。王婆便道:「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綢絹,放在家一年有餘,不曾得做,虧殺鄰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。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,縫的又好又密,真個難得!大官人,你過來且看一看。」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,一面喝采,口裡道:「這位娘子,傳得這等好針指,神仙一般的手段!」那婦人低頭笑道:繡旁來了。張旁二低頭笑。「官人休笑話。」西門慶故問王婆道:「乾娘,不敢動問,這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?」王婆道:「你猜。」張夾如畫。西門慶道:「小人如何猜得著。」王婆哈哈笑道:「大官人你請坐,我對你說了罷。」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。那婆子道:「好交大官人得知罷,你那日屋簷下走,打得正好。」張夾偏點出。西門慶道:「就是那日在門首叉竿打了我的?倒不知是誰家宅上娘子?」婦人分外把頭低了一低,笑道:張旁三把頭低了一低笑。張夾描婦人有心。妙甚。「那日奴誤衝撞,官人休怪!」繡眉嬌情慾絕。西門慶連忙應道:「小人不敢。」王婆道:「就是這位,卻是間壁武大娘子。」西門慶道:「原來如此,小人失瞻了。」王婆因望婦人說道:「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?」婦人道:「不識得。」婆子道:「這位官人,便是本縣裡一個財主,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,叫做西門大官人。家有萬萬貫錢財,在縣門前開生藥鋪。家中錢過北斗,米爛成倉,黃的是金,白的是銀,圓的是珠,放光的是寶,也有犀牛頭上角,大象口中牙。他家大娘子,也是我說的媒,是吳千戶家小姐,生得百伶百俐。」因問:「大官人,怎的不過貧家喫茶?」
西門慶道:「便是家中連日小女有人家定了,不得閒來。」婆子道:「大姐有誰家定了?怎的不請老身去說媒?」西門慶道:「被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親家陳宅定了。張夾寫生平得意事,有體面事,開頭便到。寫盡人情也。他兒子陳敬濟才十七歲,還上學堂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,他那邊有了個文嫂兒來討帖兒,張夾又出文嫂兒。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,張夾又出薛嫂兒,百忙卻句句是正中偏有此閒筆,文。妙,妙。同做保山,說此親事。乾娘若肯去,到明日下小茶,我使人來請你。」婆子哈哈笑道:「老身哄大官人耍子。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,他們說親時又沒我,做成的熟飯兒怎肯搭上老身一分?常言道:當行壓當行。到明日娶過了門時,老身胡亂三朝五日,拿上些人情去走走,討得一張半張桌面,到是正經。張夾總是以「保山」二字刺入金蓮心中。怎的好和人鬥氣!」兩個一遞一句說了一回。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,口裡假嘈,那婦人便低了頭縫針線。
水性從來是女流,背夫常與外人偷。
金蓮心愛西門慶,淫蕩春心不自由。
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,恨不得就要成雙。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,遞一盞西門慶,一盞與婦人,說道:「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。」旋又看著西門慶,把手在臉上摸一摸,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。張夾至五分光,忽然點出,則前後十分光,不言皆出。自古「風流茶說合,酒是色媒人」。王婆便道:「大官人不來,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。一者緣法撞遇,二者來得正好。常言道:一客不煩二主。大官人便是出錢的,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,虧殺你這兩位施主。不是老身路歧相煩,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,官人好與老身做個主人,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,與娘子澆澆手,如何?」張夾一路說來,純是定挨光時說過的話,乃一一重說出,卻使看者不覺其重,故妙。西門慶道:「小人也見不到這裡,有銀子在此。」便向茄袋裡取出來,約有一兩一塊,遞與王婆,交備辦酒食。那婦人便道「不消生受。」口裡說著恰不動身。張旁一不動身。王婆接了銀子,臨出門便道:「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,我去就來。」那婦人道:「乾娘免了罷。」卻亦不動身。繡眉身不動處;正是心動處。張旁二不動身。王婆便出門去了,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。
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,只看著那婦人。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,又低著頭做生活。張旁四低頭做生活。張夾寫得如火如錦。不多時,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、熟肉鮮鮓、細巧果子,歸來盡把盤碟盛了,張夾必寫見成東西,寫婆子恐怕撐開,心事如畫。擺在房裡桌子上。看那婦人道:「娘子且收拾過生活,吃一杯兒酒。」那婦人道:「你自陪大官人吃,奴卻不當。」那婆子道:「正是專與娘子澆手,如何卻說這話!」一面將盤饌卻擺在面前,三人坐下,把酒來斟。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:「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杯。」婦人謝道:「奴家量淺,吃不得。」王婆道:「老身得知娘子洪飲,且請開懷吃兩盞兒。」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,向二人各道了萬福。西門慶拿起箸來說道:「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。」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。一連斟了三巡酒,那婆子便去燙酒來。西門慶道:「小人不敢動問,娘子青春多少?」婦人低頭應道:張旁五低頭應。「二十五歲。」西門慶道:「娘子到與家下賤內同庚,也是庚辰屬龍的。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時。」婦人又回應道:「將天比地,折殺奴家。」王婆便插口道:「好個精細的娘子,百伶百俐,又不枉做得一手好針線。諸子百家,雙陸象棋,拆牌道字,皆通。一筆好寫。」西門慶道:「卻是那裡去討。」王婆道:「不是老身說是非,大官人宅上有許多,那裡討得一個似娘子的!」西門慶道:「便是這等,一言難盡。只是小人命薄,不曾招得一個好的在家裡。」
王婆道:「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。」西門慶道:「休說!我先妻若在時,卻不恁的家無主,屋到豎。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,都不管事。」婆子嘈道:「連我也忘了,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?」西門慶道:「說不得,小人先妻陳氏,雖是微末出身,卻倒百伶百俐,繡眉語俱有意。是件都替的我。如今不幸他沒了,已過三年來。今繼娶這個賤累,又常有疾病,不管事,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。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?在家裡時,便要嘔氣。」婆子道:「大官人,休怪我直言,你先頭娘子並如今娘子,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,這一表人物。」西門慶道:「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兒風流。」繡旁妙。繡眉如此情意,較武二官何如?那婆子笑道:「官人,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,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?」西門慶道:「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。我見他是路歧人,不喜歡。」婆子又道:「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卻長久。」西門慶道:「這個人見今已娶在家裡。若得他會當家時,自冊正了他。」王婆道:「與卓二姐卻相交得好?」西門慶道:「卓丟兒別要說起,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。近來得了個細疾,卻又沒了。」婆子道:「耶樂,耶樂!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,來宅上說,不妨事麼?」西門慶道:「我的爹娘俱已沒了,我自主張,誰敢說個不字?」王婆道:「我自說耍,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!」繡眉遠在千里,近只目前。西門慶道:「做甚麼便沒?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,自不撞著哩。」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。張夾將上文一總。王婆道:「正好吃酒,卻又沒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撥,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?」西門慶便向茄袋內,還有三四兩散銀子,都與王婆,說道:「乾娘,你拿了去,要吃時只顧取來,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」那婆子謝了起身。睃那粉頭時,三鍾酒下肚,哄動春心,又自兩個言來語去,都有意了,只低了頭不起身。張夾以上只用西門、婆子互相自嘈,寫婦人,止用五「低頭」,兩「不動身」,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動,而結以「只低了頭」,「不動身」,總上一段,是好筆力。又使王婆、西門一遞一句內,無不眼中有一婦人也。正是:
眼意眉情卒未休,姻緣相湊遇風流。
王婆貪賄無他技,一味花言巧舌頭。
文回文禹門云:天下事有視為極難,而作去甚易者;亦有視為甚易,而作去極難者。世上原無印板情事也,有胸中欲說之話,而臨時竟用不著者,有意外不經之談,而觸機竟道出者。大凡一言一事,皆令人料定,便無甚趣味矣。挨光一回,有誇為絕妙文章者,余不覺啞然失笑。文字忌直,須用曲筆,文字忌率,須用活筆。挨光一層,早被王婆子全已說破。此一回不過就題敷衍,略者詳之,虛者實之,兩回仍是一回也。
故《三國誌》中,每設一計,只用附耳低言,如此如此,使人急於要看下文,方知如此如此,原來如此也。若事前合盤托出,則下文仍是如此如此,又安得謂為絕妙文章哉!余頗不喜看此一回,以其味同嚼蠟也。喜看此回者,必是淫心蕩漾,意欲仿而行之者也。曾一思調情豈有定法乎?按著則例,依著步武,順著次序,前去偷人,其不挨大耳刮子也,算是他祖宗有靈。
按:「有誇為絕妙文章者」,系指張竹坡原評:「妙絕十分光,卻用九個『便休』描寫,而一毫不板:奇絕,妙絕!」
